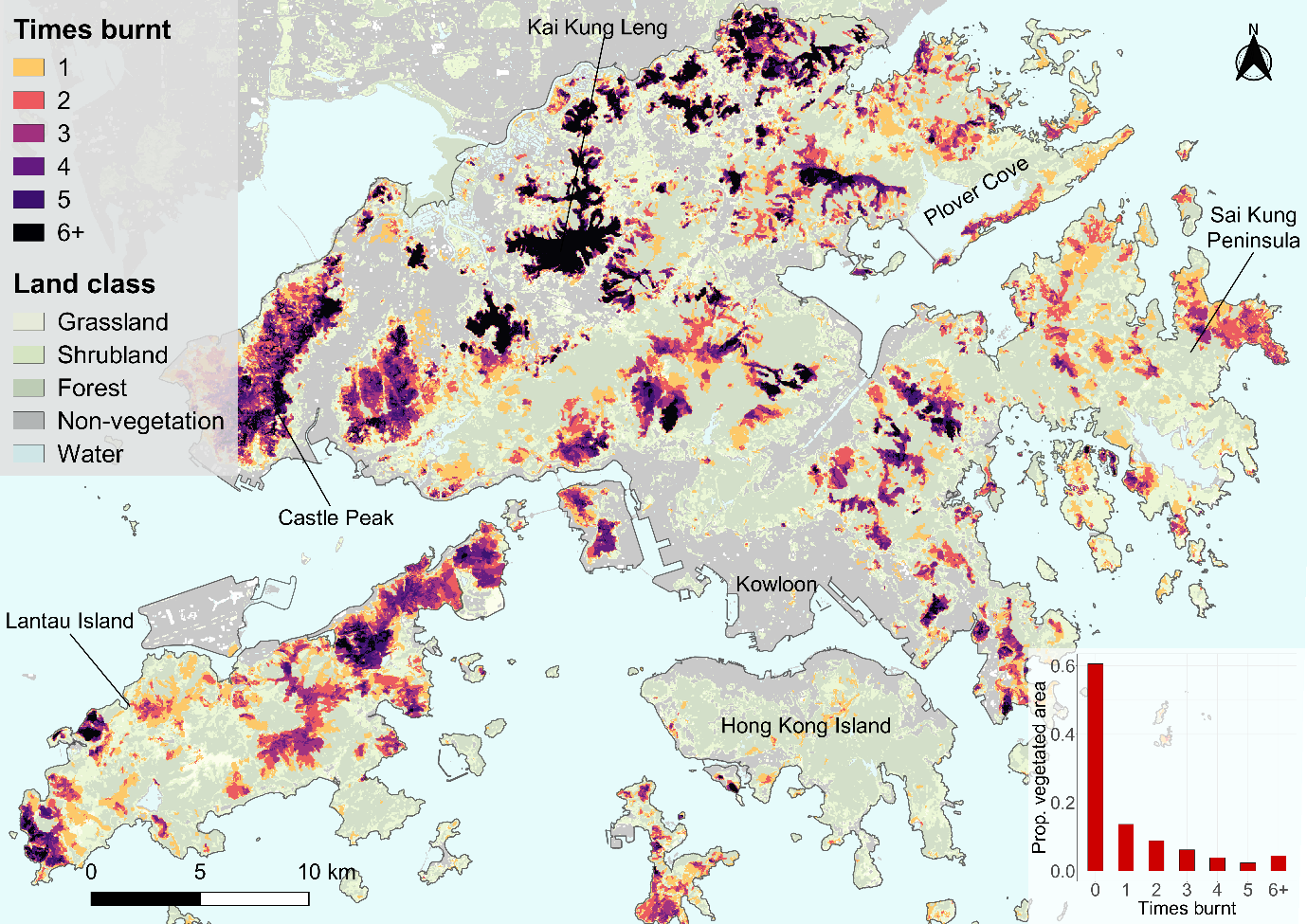文。攝:Teddy LAW(Parks and Trails)
早年獲邀進行焦點群體訪談,被問及到訪郊野公園的目的,赫然發現除了行山、跑山和燒烤等活動以外,「執垃圾」也在列。近年行山郊遊,常見坊間團體組織清徑活動,也有山友自發淨山,淨山清徑隱隱成為熱門的野外活動之一。

近年行山時常會遇上自發淨山的山友。

坊間不少團體也會舉辦清徑活動,TrailWatch 不單在其手機應用程式附設舉報郊野破壞的功能,也不時組織「執山」活動,與公眾或企業團體一起「執靚」座山。
淨山成日常活動,參與者眾,令人喜憂參半。大眾不再只是追求享樂,也意識到權利的另一端尚有義務,此為喜;山野垃圾的數量雖遠不及海洋廢棄物般源源不絕,卻又俯拾皆是,長執長有,此為憂。
回想淨山之初,沒受任何道德感召,只是抱著打掃家居般的心念,攜著夾鉗和膠袋,沿路俯拾垃圾,試圖還原郊野面貌。淨山確具短暫實效,但反復面對著形形色色的垃圾、遍地開花的「廁所位」,假想著一個個無從追究的破壞者,無法宣洩的負面情緒少不免縈繞在心。
一旦淨過山,那怕是細碎難辨的垃圾都逃不過雙目,像陡然揭開掩藏已久的一道傷疤。行山又淨山的微妙之處在於,沿著山徑前進和撿拾之際,同一時地邊欣賞山嶺海岸之美,邊直面郊野垃圾之惡,喜惡兩種相悖的心情糾結在一起,無從分割。然而內心知性的部分又不欲將二者完全割離。自顧自地玩樂,對郊野破壞視而不見,未免脫離現實;若只為淨山清徑而走進山林,過度沉浸其中,抑或常被憂戚佔據卻也大為不妥。有時我會特地「放一天假」:今天只去行山,垃圾就不撿了。適時放過一下自己,看顧自己的情緒,是淨山和坊間不少團體也會舉辦清徑活動,淨灘者的必修課業。
有些人會質疑,清潔山野海岸只是為破壞者代勞,無異於鼓勵別人肆意丟垃圾;向山海釋出的善意反會被利用,讓他們的罪咎感獲得釋放。我無法驗證箇中因果關係,但試想想,一個缺德之人在行惡前還會在乎有誰替他善後是何其荒謬。這好比「林超英冇開冷氣,我可以放心開冷氣」的調侃言論一樣,只能付之一笑。
若然旁觀者只注目在撿垃圾這個舉動上,而非視之為教育和轉念的契機,又或行動者只滿足於清理大量廢物的輝煌戰跡,而不嘗試去尋根究底,只會將淨山的焦點錯置。一再追問之下,你必會發現適當地處理垃圾、帶走自己垃圾此等基礎公德意識已遠遠不能回應如此棘手的環境問題。撿垃圾是一面溯源一面內觀,透過行動來自我拷問:垃圾何來?棄者為誰?而我們當下又能做些甚麼?
城市生活的便利,無疑造成山林的額外負擔。這幾年間,我逐漸覺察到登山者只是轉換了身分、切換了場景的城市人。其實我們與破壞者的距離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遠,彼此同是垃圾的源頭製造者之一,也抱持一般的消費觀。我們與埋在某處山頭落入某片海洋的那些垃圾終究脫不了干係。

我們不單需要提升大眾的減廢意識,也要改變疏於節制的消費觀念。

不少淨山和淨灘者都會身體力行,由行動自覺再進一步成為環境教育倡導者。
淨山清徑,既撿起被遺棄的山野垃圾,也拾回城市人丟失的環境責任,是將每一次的行動逐步內化成覺知,並且持續在生活中踐行。
就讓兩種情感繼續交織碰撞吧……領受山海賦予的喜樂,也同時承受她的憂與悲,休戚與共,也許是我們無可卸卻的責任。